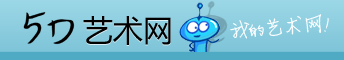#12001/7/11 7:14:24
清晨一地鸡毛
红尘
尽管节食减肥是现代女性的时髦,然而,那些饿肚子的日子,却总是那么令我终生珍记。
冬天,总是我们弹尽粮绝的季节。
知青过日子,没有人费脑子去筹划打算,月初领了粮食胡吃一通,月底的日子很煎熬,尤其是冬天。
长睡不起,是我们冬闲时的保留节目。隔壁的男生敲着薄薄的泥墙说:“起来吧,今晚有好吃的。”
向晚的炊烟与暮岚相融出一派旷古的静谧时,男生猎人一样用草结的绳子捆扎了他们尚称不上魁梧的腰身,绕过院墙,沿小路出村去了。那一瞬,严峻的表情令他们只有一抹绒绒胡须的脸庞有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气度,很是令我们由衷地欣赏了一阵。偷猎大概比打猎艰难,免不了会有做贼的慌乱,并且他们是初犯。苍白的冬月已偏移至午夜时分,勇敢的猎手还没有归来,守着油灯,闹革命的肚子也已疲倦,唯有做女人少不了的担心在猜想,也许他们已让外村的农人抓获,正被绑在村头的大树下,明亮的火把令他们青春的脸无处躲藏。
男生喊醒我们时,两只鸡已逶迤在血泊中。那顿夜饭做得真是鬼崇,大家全阶级敌人一样,说话时尽可能地压低嗓门,兴奋的眼睛在昏暗的油灯中乌亮闪光。一旦听到门外稍有动静,全屏住呼吸呆若木桩。两只鸡很快被我们5 个年轻的齿咀嚼填入腹中,啧着油汪汪的手,我们还有意犹未尽的遗憾。
男生钟建说:“把这堆鸡毛用土埋了,不要留一丝痕迹。”他指挥员似地冲我们一挥手,我们认真地点头应允,一点都不觉得他可笑。那些被火烘干的鸡毛,有的真美,尤其是芦花鸡毛,若在平常我一定要捡一些夹在本子里,待做毽子时用的。我们刚刚埋上鸡毛,就听到村东头传来鸡受惊的叫声,不祥之兆把我们三个女生定在院中,就有踏踏的脚步声急速而来。气喘吁吁的他们一进门,拽着我们就往厨房躲,机敏的钟建一口吹灭了那盏昏暗的油灯。我是那么清晰地听见咚咚的心跳从他俩胸腔传出。
一会儿,就有纷乱的开门声和零星的脚步声使乡村的夜失去了宁静。
人们纷纷燃了火把,查看自己家高卧在树上的鸡群。好不容易夜又在各家的关门声中静了下来。我们才怀着不安各自回房睡下。吃得饱饱的觉也睡得香沉,后半夜的风雪交加一点也没有搅动我们的安睡。
被人喊醒已是正午饭时,“睡死了,饭还吃不吃。”这位叫镐京的农民小伙儿是我们知青的铁哥们儿。走出房门,我惊呆了。那些红的、芦花的鸡毛在雪地的白布景上,像开得耀目的花儿,镐京一边用扫帚收拢它们,一边斜目看着我们,用知青们流行的口头骂,狠狠地骂了我们一句。
聚在热坑头上聊天,是农人们雪天的娱乐。有关昨夜鸡惊则是重复率最高的话题。有人猜测说是黄鼠狼,有人认定是狼,理由是他家猪圈旁留着狼的蹄印,说这话的就是镐京。后来又有外村的亲戚说:“你们这儿还好,只是虚惊,我们河滩村1 0来只鸡都被黄鼠狼拉走了。”我们听后面面相觑,难道昨夜还有跟我们不谋而合的知青,也偷袭了河滩村。回来后,我说他们也太狠了,怎么就偷人1 0来只鸡呢?钟建就对一旁脸黑如炭,有一双乌亮小眼的镐京说:“我们只偷了两只。”镐京又骂我们一句,这次我们统一还击他,然后大笑,笑声中桃树上的积雪落英般飘洒。
接下来的日子,虽仍是冬闲却再也没有睡懒觉的机会了。一大早就有人从我们可偷渡过肥猪的栅栏门钻进来,擂着窗子喊我们懒虫,吆喝我们去吃“烤焦黄了”的玉米面馍馍。
一日,我们又浩浩荡荡开进了“神婆”大妈家,围在灶前一边声音很响地喝她熬得金灿灿的玉米粥,一边开玩笑:“神大妈,不怕我们吃穷你吗?”“神婆”睁着她那双大得似乎合不拢的眼睛,笑着说:“你们吃饱了,咱村就不闹黄鼠狼了。”一低头又从灶肚内掏出焦黄的馍,塞给我们一人一半,却把她流着鼻涕的小孙子堵在门外。
其实,我们那点小伎俩,岂能瞒过这些世世代代跟偷袭家禽的黄鼠狼之类斗智的农人呢?他们什么都知道却用乡里人的宽容和厚爱来包涵我们,实在是因为他们心底的善良。感动之余,我们再也不曾滋生偷猎的念头。
有时候善和宽厚的行为是强有力的道德规范,我们不想破坏它。
偷猎那年,我们刚刚18岁,与那些爱我们的农妇的孩子同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