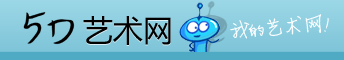|
|
主题: 保重自己
|

秋冰梦
职务:普通成员
等级:6
金币:5.0
发贴:4325
注册:2002/5/16 22:14:21
|
#12002/9/30 15:37:45
人,这不伦不类的物事,只有一点我们最清楚无可奈何地张大了嘴,我们降生在这个夸张的世界里。吃一惊的也是:我们的嘴真大。我坐在北上的列车上,车下人潮汹涌摩肩接踵,道别的祝福和难舍难分的叮嘱接连不断地传入我的耳中。我凝视着车下的吴悠她的身影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最后落在我视觉的盲点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就喜欢自言自语,喜欢幻想在我的身边会发生哪些故事。我想它们的经过和结果,一遍又一遍,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因而有许多事情我虽然是第一次发生,但对我来说已经是第二次了。这使我从少年起就对无尽的人生有了一种饱经沧桑的感觉。直到有一天,那天纯粹是个以外。我记得那天挺热的,高考的成绩还没有下来,我给一个在地安门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就奔那去了。我下了公共汽车往南走,我走的很慢,因为我喜欢看忙碌的人群,和人群中美丽的女孩子。就在前面不远处,在路边,在灼热的阳光中我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她雪白的皮肤象“可爱多”冰激凌一样诱人。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我清了清嗓子走上前去。我在她的身边站了一会“今天挺热的啊”我说。姑娘侧头冲我一笑,点了点头。“您知道地安门怎么走么?”“我不是这的人,我也不清楚。”“那你去哪呢?”我往下发展。“你就别套瓷了,去哪我也不去地安门。”说完她笑了,那是种叫人很尴尬的笑容,我觉得有狡猾的成分在里面。我上当了。这种钉子我碰过不少,现在的小姑娘都变的精了。从世界是物质的角度来说我没少什么而她也没得到什么。可我还是挺撮火的,张着嘴不知道往下我该说什么。她是头一个叫我有这种感觉的女孩子。我扭头就走了,心里狠狠地说:牛什么呀。我没去我哥们那,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站了许久。来自祖国各地和国外的游客们在纪念碑座下的汉白玉栏杆中象鱼一样川流不息。我微笑地接过游客们递来的相机帮他们拍照,他们都用热情的“谢谢”来回报我的举手之劳。那会我就在琢磨象我这样的人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等我逛到了前门,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赶紧往家赶。路过北图的时候,我决定先不回家了。北图的放映厅的门口聚集了不少的人,肯定有什么好的电影了。我给家里挂了个电话就奔那去了。片子是冯小刚导的《遭遇激情》。票早以售完。门口的人一半是等人的,另一半是等退票的。我的眼光左右搜索,最后落在坐在远处台阶上的一位女孩子的身上,她的皮肤白的象“可爱多”冰激凌。我看见她的时候她也看见了我。我躲进人群,有种小偷被警察发现的感觉。我的眼光开始去找那些时不时低头看表而面带焦急的人。终于,一个小伙子最后看了看手表,手伸进了裤兜。他的票还没拿出来,我已经站在他的身边了。“您有多的票么?”“有啊,你要几张?”“一张就够了,我也不能一个人占两个座啊。”“是啊,你倒是想呢?给你,我着刚好有一张。”我把钱递给他,他怎么也不要。这时候他的机响了,他低头看了看,然后把另一张票也塞到了我的手里:你这回可以一个人占两个座了。我等小伙子走远了,就拿出一张准备卖了。“卖给我吧。”不知何时那个美丽的女孩子已经站在我的身边了。我有点不情愿地把手中的饿票递给她(我现在也奇怪我怎么就没挤兑她几句呢,主要还是因为她漂亮吧,我想),“送给你吧,既然。你也挺想看的。”本来我想说是反正也是别人白给的。“你怎么知道我想看?”“那你做那干嘛?”“我可以等人啊”我有点气了,“那你继续等吧,把票给我。”说着我伸出手。她笑了声就跑了。我也在笑你跑有什么用?咱们是挨着的。从放映厅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了她的名字吴悠。吴悠,无忧,还有个象声词“唔呦”,这个名字太好记忆了。她看上去和这个名字倒是满般配的。她笑着问我:“你当时是不是挺生气的啊?”我没有回答却问她:“你是不是贫血?”“不不,我不是电影里面的那个女的,我虽然白点但我很健康。你是不是就盼我有点病有点在什么的?就因为我叫你碰了个钉子?”“你也别把人都想的太坏。就算我挺生气还没到咒你的份上。再说了,我那也就是一般的讨好吧?”“还是说实话了吧。反正也不能想的太好,你们这样的对谁能安好心啊?回头被你给卖了还帮你点钱呢”“那不见得,就拿我来说,你曾那么冷淡地对待我可我依旧以热情来回报,也不管心里是多么的撮火,”我看了她一眼,她的表情就象是个很大度的智者,我收住了我滔滔不绝的话“这是事实吧?”“哦,你是说你挺大度的是么?”“不,我的优点还不止这些。”“那我怎么没看出来?”“当然了,时间太短了,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那好吧,我没钱回家了。”“你看你看,得寸进尺不是?”我用手指点着她。她的脸红了,也,更好看了。后来,她回家了。给我留下了她的电话,我也把我的给了她。以后的几天里我时常想她。她曾来过电话但我都不在,我也曾打很多个过电话给她,都是她家里人接的说她不在并问我是谁。我乱想了个名字就挂了电话。分数下来了,我能上个本科,几个好朋友也都有学上,这就挺叫人高兴的。那天大伙聚在了一起,七个人喝了一箱半的啤酒。只有支军没有倒下,他把吐的天昏地暗东倒西歪不分厕所和厨房的我们一个一个拖到了洒满阳光的阳台。我躺在那里头脑很清醒,感觉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我反复说服自己没醉但怎么也站不起来。这时,支军拿着一部分离电话给我“有人找你。”“谁啊。”“反正不是你妈妈。”我接过电话,但从里面传来的“喂喂”的声音听起来很生疏。“喂,谁找我啊?”“是我。”“你是谁?”“德行!”我听出来了,是吴悠。我挺高兴的,“你怎么打到这了?没看出你的能耐这么大啊?不是按电话本的顺序挨个打的吧?可有几十万个呢。”“你妈妈告诉我的。”“有什么事么?”“没什么,就是想给你打一个。老找不着你。”“是想请我吃饭了吧?别不好意思,我答应你,说吧,在哪?”“你喝酒了?”“喝了几瓶。”“你不象蒙古族的啊?那么善饮?醉了?”“没有啊。我还是五个手指拿着电话和一个美丽的女孩子在聊天,不,该说是羞花闭月,沉鱼落雁什么的。”“哦,那是喝的多了点。醉了。”过了半晌,她又说:“我家人叫我小心点呢。”“小心什么?小心谁?谁欺负你了?”“你!你三天两头地给我打电话。就你才危险呢。”“那你还来电话”“算了,算了,今天是不行了,明天吧,我给你打电话。”说完她挂断了电话。我拿着响着忙音的电话发了会呆,才把电话也关掉。我祝自己能天天开心,倒头就睡在了阳台上我躺在荒蛮的土地上看着你青春的流失,你站在光秃秃的小山上听着我的呼噜声传向四方来源水木清华站发信人,信区标题保重自己发信站水木清华站那天是我和吴悠的第一次约会,她选在了玉渊潭。我们一见面就聊到了一起。象认识了很久似的。她说的少,我说的多,大都是发生在我和我身边的一些趣事。她听的很认真甚至有点虔诚。这使我想到了孙敬修爷爷给小朋友讲故事。“我说,你别那么看着我,一眼不眨地,这会使我有犯罪感的。”“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阴谋?”“不,没有,至少到现在还没有。”“那你就不怕我有点什么企图?”她说话的样子很认真。“你别吓我啊,我胆小。”“等着吧!”她说。聊着聊着,她突然问我:“你想过出国么?”我一愣,说:“首先我没那个本事,其次我也不想。待在祖国的怀抱里有什么不好?有吃有喝的。当然了,我支持别人出去,要是咱们的人都出去了,咱们就把世界给统一了。再说了,都走了,我就守在这块根据地,等着那些出去的人被反压迫的人民给赶回来。”接着我问她:“你是不是想走啊?”她点了点头。“小心啊,”我说“别回头在外面连回家的路费都被骗走了。”“你是不是总这么说话啊?”“不啊,聊天么,就得聊的热闹些么。咱们不能只靠眼睛来表达吧?”“我宁愿你一句也不说。”“那好吧,我就象鱼一样沉默。”除了聊,我们当然也玩,等玩够了碰碰车,翻滚列车等各种电动游戏,我们厚着脸皮爬上了儿童的滑梯一遍又一遍地滑下来。我们玩的很开心,很多小朋友和我们一起玩,他们的父母就看着我们笑。我估计要是没什么人的话,他们也会爬上来玩。然后就是吃,当我们花光了兜里的最后一分钱,当我们把肚子里塞满了话梅,汉堡,冰激凌的时候,吴悠忽然问我:“咱们怎么回家呢?”我们走到了汽车站,我说:“咱们和售票员说说,也就行了。”“我的脸可没你那么厚,我不去。”“你的家在哪里?”“亚运村。”“你不是想叫我背你回去吧?”“你要走就走么,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有点生气了,“那好,你自己等吧,看看哪个好心的人能救你!你真不上啊?车都来了。”她变的好象不认识我一样,没理我。我没理她,上了车。但,在开车的一瞬间,我又下来了。“神经病”,我听到售票员在说。她没说话,对我怒目而视。我忽然想起在四道口有个朋友。我们是走着去的。一路上我开了几个玩笑吴悠始终都没笑,只是侧着头看着我听我不停地说。天色暗了下来,路过钓鱼台国宾馆的时候有一列外宾的车队从里面开出来,前面的开道车发出了刺耳的警鸣,后面车队从我们的身边驶过,尾灯在夜幕下闪闪烁烁,浮浮凸凸。直到我在四道口把吴悠送上了出租车,她才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恨死你了。”当时我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糟了。后来,这事就成了我时常被挤兑的依据。吴悠说:“你就那么傻?叫你多陪陪我怎么了?你还不乐意了啊?真是的,还以为你挺善解人意的呢。”我要么是打叉,要么就用“嘿嘿”的傻笑来掩饰自己的理亏。从哪天起,我们家里的电话费就高上去再没下来。父母见到我拿着电话眉飞色舞的样子十分诧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在恋爱了,虽说我挺无聊但我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我曾见过我有的朋友因为女孩子而烦闷和痛苦的样子,我不想变成那样。我下过决心的,但吴悠的一个电话就把我所有的斗志瓦解了。父母开始干预我们的来往了,但都被我们的铜墙铁壁给挡了回去。我觉得我们牢不可破了。吴悠比我小两岁,但也参加了高考,不久我和她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庆幸的是我们都留在了北京,在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开学了,她在人大读外语系,住校;我在联大电子读无线电,走读。我们还是经常见面,也聊天。但,渐渐的,我没什么可以和她说的了,有时我去她家里或是学校找她,她也是忙着自己的事情,不怎么理我。有时她见我一付游手好闲的样子,微微皱了皱眉头欲言又止。这使我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被人冷落的不自在。一次,我去她家找她,刚巧她在家,一个男孩子也在,帮她收拾阳台呢。那个男孩子短短地自我介绍说他叫李辉,是吴悠的同学。我们寒暄了几句他就继续帮吴悠去了。吴悠干活的时候我从不插手,我干活的时候也不喜欢她插手。我走到屋子里随便翻了翻桌子上的杂志,没什么意思,于是我就站在边上看他们干活。阳台已经收拾出了一大片的空地,我打趣地说:“就是,这么一来地方大多了,可以种点菜养头猪什么的。是吧?”吴悠白了我一眼,说:“谁象你啊?好吃懒做,这块地方就是给你的你知道么?”“那好啊,我还用自带铺盖么?”她不理我了,看看收拾的差不多了,就招呼她的同学进来休息。吴悠从冰箱里拿处可乐给李辉和我,他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李辉的眼光紧随着吴悠的一举一动,好在吴悠对我依旧热情(我喜欢她这样在外人面前总是给我面子)这使得李辉看我的眼光中夹杂了一丝的敌意。“你是学无线电的?”他问我。我想是吴悠告诉他的,就点头说是。“你们理科的课紧么?”“不,一点也不。很轻松,我们经常和老师在课上探讨人生。”李辉对我的回答不以为然。我们三个就随便聊,天南海北,芸芸众生。但聊到了人的本性的时候我和他们的意见有了分歧。他们认为人是积极的,可我的意见刚好和他们的相反“你说,比如,人类的创造不是积极的么?”“那也是因为懒惰,要是都爱走路的话,那要马和汽车干嘛呢?”“你考虑问题太偏激了,走了极端。”“你是说要辨证地来看,是么?”“是啊。”“矛和盾本来就是一体的,是认为分为的对立。”“你的思想太偏激了。那你追求的是什么呢?”“我?只是两饱一倒。”“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呢?”“我说,咱们就别老是思想啊意识啊什么的。思想是什么?思想就是一把伞,只有太阳太大和下雨的时候人们才会打开它来对付风雨。谁也不会没事的时候拿把伞打在头顶。”我漫不经心地把话说完,带着微笑看着李辉。我看了吴悠一眼,她看我的眼光很失望。我们没有再讨论什么,不久李辉就起身告辞了。我干坐在那里,吴悠的眼光盯在地板上一语不发。我厌恶这种沉闷,站起身朝门口走去。吴悠突然站起身跑到门口挡住了我的去路。她的眼睛睁的大大的瞪着我,我不敢去面对她的目光。“怎么了?觉得我不是你想的那样吧?失望了?还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她先还是瞪着我,但忽然,嘴巴瘪了瘪竟哭了。我就知道她看清了我就会后悔的。我也挺难过的,说肝肠寸断过了点,但是我是真的难过了。我觉得自己也该改一改了,我打算好好学点什么要么就是干出点什么。我不想叫她那么失望,因为我发现我离不开她了。从那天起的一个星期里,我回家都很晚。我对我妈妈说去了计算机房上机但实际上我是去了朋友家打电子游戏和看录象去了。吴悠还是经常给我来电话,正因为我知道她会给我打电话我才这么干的。那天我回家比较晚,一进门就看见了吴悠,正和我妈聊天呢。我回自己的屋子时她也跟了进来,象个小丫头似的笑着看了我老半天。我知道她正在为我的努力而高兴呢。我们一起吃的晚饭,饭桌上我妈不住地给她加菜,她就象个特别守规矩的小姑娘,一句话也不多说。我妈可不知道她在我面前有多不讲理。不管怎么说,我喜欢这种和谐的气氛。吃完了晚饭我送她回学校,她笑着对我说:“你妈怎么老夸你啊?”“我妈也没少夸你吧?快告诉我,我妈都说我什么了?”“说了你小时候光彩的故事,我还看了你的百天的照片呢。”“那是我妈看中了你,想把你收编变成自己人。是不是我去了你家,你妈妈也能这么对待我?别老盯着我跟盯贼似的。”“那得看你的表现了。你怎么好象瘦了啊?”“别别,你要夸我你就直说,我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我本来还想呢。你要是老这样就算了。”“你看你看,就这么经不起考验。拿出点舍死忘生的执着精神么。”“你就不能把嘴巴闭上么?”我们又象从前一样了。吴悠总盼着我能干出来点什么。只有我自己才知道这里蕴藏了多少危机。有时候我也有点害怕,但日子一天天都过的很好,我也就放宽了心。我依旧是饿了吃,困了睡,想吴悠了就买上一堆好吃的去学校找她。但是,我的话越来越少了,我知道自己是往什么方向走。那天我做了个梦,梦里有好多的人在追我,我玩命地跑直到跑不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在另一个星球。我的周围什么都没有,我好象是被悬浮在空气里,我眼睁睁看着我的冷汗在身上冰凝。醒来后我一身的冷汗瑟瑟发抖我,真的害怕了。日子在一天天地过去我躺在荒蛮的土地上看着你青春的流失,你站在光秃秃的小山上听着我的呼噜声传向四方来源水木清华站发信人,信区标题保重自己发信站水木清华站我被开除了,原因是旷课太多而期末考试不及格。我连补考的资格都没有。任课老师说在课堂上就没看见过我,所以学院就给我放了个长假。妈妈知道后伤心地哭了,爸爸,这个曾带出了许多研究生的老教授只是痛心疾首地看我我一眼,摇了摇头。从此我一个人在家,很孤单。家里的电话费也降了下来,从我被开除那天起,吴悠就再没来过电话。我打过许多电话找她,但接的人都不是她。有一次我觉得接的人是她,但我刚“喂”了一声那边就挂断了。我觉得我们完了。我经常一个人面对着一个空旷的大房间,从前我喜欢看的书和喜欢干的事情现在我都没了心情。后来,爸爸突然叫我去学俄语,说学好了就给我找个不错的工作给我。我在家不能总这么闲着,当然,在家里我早就没有了发言的权利了。我真的开始学了,换句话说我发奋了。俄语的发音不象英语,它发音的时候舌头要不断的打嘟噜,一个单词多念几便舌头都木了。我还是经常想吴悠,我想她会有新的男朋友,有一个新的生活圈子,我对于她来说也许就是人生的一种经历吧。可没有她,我总觉得少了什么似的。两个月后,我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了。爸妈对我的态度也渐渐的好了。一天,爸爸来检查我的口语能力,之后满意的点了点头,他说:“你要是早这样就好了。接着他又说:“好好学,别半途而废。你不想回老家种地吧?”我爸的老家在农村,我知道他是说一不二的。“你得知道,社会以后容不下那种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你以后迟早要自己养活你自己的。”“那我什么时候能干您说的那分工作呢?是不是当个翻译啊?”“你行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你继续学吧。”说完,他带上房门让我继续学习。天气渐渐的热了起来,我的俄语水平也进展的很快。吴悠来了,是在我家里待了快半年的时候。她比以前漂亮了,我是说,一看就是那种出类拔萃的女孩子。我客气地把她让进家里。对她的到来我先是喜悦,但我也有种说不出来的伤感。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走了。我从冰箱里拿出可乐给她,她还是笑着看着我,眉目中流露着喜悦。我对她的突然造访大惑不解,而且我猜不透她来的目的。我总觉得她的笑里有狡猾的成分。她问东问西,我说的很少。“你怎么不夸我漂亮了?”她带着笑看着我。“挺好看的。”“是你的真心话么?”“我说吴悠,夸你的人不少。你怎么非要听我这一句呢?你不是那俗人就别往自己脸上扑粉了好不好?你怎么变了?”“人是会变的啊。你不是也变了么?这么深沉!”我对她的这种口气不太习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有过花前月下的那一段日子。就说:“别挤兑我了。你有什么事情就直说吧。”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东拉西扯地聊着她学校里发生的故事,而且她不时地低头看着手表,就象等着一颗快要爆炸的定时炸弹。我也看了看手表,表的指针指向了下午五点,它唯一能提醒我的就是我爸妈都下班了。不久,楼道里各家的门开了又关上,水龙头哗哗的流水洗菜的声音也传了过来。爸妈也回来了,妈妈一见到吴悠就热情地打着招呼。我真不明白,我被开除的那几天她还唠叨人家呢。“叔叔好,”吴悠看见了我爸热情地叫着,然后就跟着我爸去了书房。我对此大惑不解。不一会,我爸叫我进去。我站在他和吴悠的面前,吴悠依旧笑着看着我。忽然我爸开口了:“你准备一下,过几天去体检,然后去办签证。”签证??我的头轰的一声,我要出国了?“您不是把我当劳工给输出了吧?”“比那好多了。”“是去当翻译么?我还差的太多了。”“你去了就知道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没想到竟然会要离开这块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地方,不,我不想去,尽管有许多人削尖了脑袋想往外跑,尽管我听说许多人从外面功成业就地发了财回来,我也不想出去,我喜欢这里。我想辩解,但我看到爸爸那眼神我就知道一切争辩都是多余的。我头脑中很乱,等我可以清醒的考虑问题的时候,我断定这一切都和吴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吃完晚饭后,我借口出去走走把吴悠也拉了出去。路上我一把拉住她问道:“我怎么你了?你非要把我给卖出去?”“你?你怎么还是这样?”“我怎么了?”“你骗了我。那会你根本就是在玩。还骗我和家里你去上机了。你知道我听说你被开除了有多伤心?我哭了好几天呢。”原来她也为我难过,这使我感到错怪她了。那也别从此音信皆无啊?“我也挺难过的,是真的。不仅仅是为了开除的事。”“得了吧你,我看你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呢。可以放心的去看录象和打电子游戏吧。”怎么她连这个也知道?“我没闲着,在家里学俄语呢。”我为自己辩解着。“那好啊。等你去了莫斯科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好好学了。”“去哪?!”原以为就是去当个蹩脚的翻译什么的呢。“独联体!那有所较郝的机械工程学院在等着接受你。去了那,你还得再补习三个月的俄语。”“新闻里说那挺乱的,时有枪战发生。”“呦。你什么时候见了事是躲着走的?那的环境适合你,再说了,送你是去念书,也不是叫你去搞政变。”“这是你的主意吧?”“我还不是为了你好,你就不能正经一回?你又不傻。”我已经有点明白她的企图了,我看着她:白皙的皮肤,小巧玲珑的身材,大大的迷人的眼睛,到哪都会有一大帮的人追她。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这么有福气。她真的是么?我不知道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和她的呢,我就更难说了。也许我一开始就错了。我不知道。“吴悠,我可以学点别的,电脑啦,财会啦,咱们别去那么远行么?”“不行!”“我总该有选择的权利吧?”“你这次没有。”“我是真的不太想。去。”我说的吞吞吐吐的。“你?!”她的眼睛睁的很大,瞪着我。沉默了好一会,“什么时候体检?”我说。那个晚上她很开心,对我是百依百顺,一句话超乎寻常的温柔。好几次我不得不把她拉到身边仔细看看是不是认错了人。我躺在荒蛮的土地上看着你青春的流失,你站在光秃秃的小山上听着我的呼噜声传向四方来源水木清华站发信人,信区标题保重自己发信站水木清华站签证和体检都很顺利,现在去那念书的人很少,大多是去当国际倒爷的。果然不出我的意料,这一切都是吴悠串通了她爸和我爸干的。她得知她爸的一个老同学可以介绍一些人去独联体念书头一个就把我给选上了。原来在我想她可能和别人开开心心玩的时候她依然在想着我,我挺感动的。和我同行的有几十个年龄相仿的学生,我们都是自费的。支军听说这事来看了我几次。他说吴悠很厉害,得知我被开除后把我哥们的家转了个遍,也掌握了我的第一手资料。“你够厉害的啊。怎么认识的?也教教我,赶明我也找一个这样的。”接着他说那边很穷,说要是带一车皮方便面去准能换辆坦克回来。吴悠的父亲也叮嘱我要好好念书,别给他在他的老同学那丢人。我点头称是。有了空我依旧是学俄语。我发觉我真的变了,而这些变化却是吴悠帮的我。这些天吴悠下了课就来陪着我,除了陪我看书也陪我上街买东西。她的心很细,连指甲刀都要买两把而且还要挑挑。我说我去的又不是非洲的难民营,她却依旧地着头在挑选。我觉得我爱上她了,而且,我越来越不愿意走了。“吴悠,我去了那会想你的。写了信你得快点给我回啊。”“你别把我叫什么给忘了我就谢天谢地了。我倒是怕你误了回我的信。”“哪会呢?不会的。不会的。你们那追你的人特多吧?”“你以为都象你似的?脸皮那么厚?在马路上就开始和人家凑近乎?”“那当然不会。不过会先请你去喝咖啡或者跳跳舞什么的,先培养一下气氛,再下手就容易多了。”“那你怎么没请我去喝点咖啡跳个舞什么的?老是我自己送上门?”她笑着说,仍然低着头给我收拾行李。我没词儿了,觉得有点失落,不仅仅因为无言以对。我站在她的身后看着她把那些她精挑细选的生活用品放入箱子。她见我没声了,转过身平静地看着我,“那你不会好好学早点回来。”她说着,脸红了。我慢慢地把她拉在怀里,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鼻子酸酸的。等我有工夫想起这一切的时候,已然是坐在火车上了。临别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少不了叮嘱我注意身体,好好学习。然后,就把时间留给了我们。我们只是相互看着,我倒是真的想把她看在眼里拔不出来了。“我的钱包里有你一张照片,你把咱们其他的照片放哪了?”“在那个最大的箱子里右边的小包里。”“我就没怎么照过相,回头你连我长什么样都忘了。”“你看。”她从兜里拿出一张照片,我一看,是我出生一百天的黑白照片,什么衣服也没穿。“你就是这么想我啊?”我说。她笑着什么也没说。车快开了,我做在位子上把车窗拉开。我拉着她的柔软小手舍不得放开。车开了。她和我的父母一起往后退了几步,一起向我挥着手。妈妈还是在叮嘱我注意身体,但突然哭了。吴悠的眼睛里也有种晶莹的光在闪动。我不住的挥手,不住地对我父母说“放心吧”。突然,我觉得有什么不对了,仔细感觉了一下才知道列车是向南开呢。“吴悠,这车怎么往南开啊?不是北上的么?”吴悠站在远处,她的微笑依旧那么迷人,我不知道她听见了没有。别着急啊,我还在修改呢,我躺在荒蛮的土地上看着你青春的流失,你站在光秃秃的小山上听着我的呼噜声传向四方来源水木清华站发信人,信区标题保重自己发信站水木清华站当我再次抓住吴悠的手的时候,我怎么也不肯放开了。我仿佛有很多的话要说,但除了静静地看着吴悠,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感觉她的手轻抚着我的脸,她的目光也紧紧的盯着我,嘴角露出了满足的微笑。“吴悠,这就是你和我们说的你的男朋友吧?也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那个冲我笑的阿姨说话了。吴悠回过头,红着脸笑了。“你看他怎么配的上你么,还是嫁到我们家吧,我表弟可精神了。”吴悠的脸更红了,还是笑。接着同病房的人都拿我开心。我也没办法反驳,只有跟着吴悠一起傻笑。午饭后,吴悠睡了一会,我看着她熟睡的样子,我轻抚她散在枕边的长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种想哭的感觉。好在吴悠醒了,她用毛巾被把自己裹起来,唯独把脑袋露在外面,大大的眼睛一眨一眨的看着我,这叫我想起了我在路上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醒了?”“醒了好久了。”“喝水么?还是吃点菠萝。”“我想去游泳了。”“等你好了我和你一起去。”“泳游不了,那我想出去走走。”“外面太热了,待会再出去么。”“我不,我想现在出去,老躺着背都疼了。”“那我去问问护士。”“德行。早知道就指望不上你。”我只有陪着笑握住了她的一只小手,坐在床边给她讲在莫斯科的很多故事。吴悠睁大了眼睛听我讲,我把很多故事讲的有声有色,病房里不时传出吴悠的笑声。晚饭过后,我才领着穿着宽大病服的吴悠来到楼后面的一个小花园里。“我要坐你腿上。”吴悠指着一个长凳撅着嘴说。我把吴悠揽坐在我的腿上,一手揽住她的小蛮腰,一手抓住她的一只小手。吴悠也双手搂住我,再没有当初在她们学校里那种战战兢兢和扭扭捏捏了。“你想我么?”吴悠问我。我没说话,把她搂得更紧了。“你知道么?我有预感你要来,真的。我总觉得你肯定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抱着很多的玫瑰。快说,玫瑰呢?哦,对了,你怎么好几个星期才给我来电话啊?真那么忙么?还是有了别的女朋友了?”我看着吴悠笑了,没说话。“我问你呢,你老笑什么啊?是不是做贼心虚?”我依旧没说话。“哎,你怎么才出去两年就真的变成鱼了?真的不爱说话了?”“那你还希望我象原来一样么?那你连插嘴的机会都没了,我是怕你回头自卑,所以才没说。”“才说你变好了呢,就知道你本性难移。不过,你瘦了很多。”说着她用手轻轻抚摩着我的脸颊。“还说我?怎么把自己给送医院里了?”“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晕倒了么。听她们说没什么大问题的。”“听谁们说的?”“是我的病友啊,她们都说住几天就没事了。”“听你父亲说还要做个很小的手术呢。”“看见你,高兴死了。”吴悠又象个小丫头似的,做在我的怀里不是揪我鼻子就是拧我的耳朵。接着她又说:“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么?”“是我们认识的时候吧?”“你怎么知道的?”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我都有点后悔了,那么快就成了你的女朋友了,一点过程都没有。我在学校的时候看别的男孩子追我们系的女生可辛苦了,天天在楼底下等。”“那我也去追你们系的女孩子,也辛苦一回给你看?”我嘿嘿的坏笑着。“你敢!”“追你的人也不少吧?我不问也知道。”“那当然了,可多了。”“你看你看,还沾沾自喜虚荣。”“你不虚荣啊?看你那会在我们学校拉着我昂首阔步的样子,我为好多人抱不平呢。”“是啊,是啊,是谁认识我就三天两头给我来电话?”“你?!那又是谁想把人扔在车站一个人回家?”我就知道翻来翻去她总得把这事情给抖搂出来,反正也没什么道理可讲,就用最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封住了她小小的嘴巴。一时间,我忘记了我们是在医院里,如果不是那股消毒水的味道,我们真的象回到了从前。在晚查房前,我把吴悠送回了她的病房,叮嘱她好好休息并且说我明天还来看她。“哦,差点忘了。”我从口袋里拿出在莫斯科给她买的胸花,放在她的手里。“听话啊,好好睡。”吴悠的笑容依旧那么迷人。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天天都去陪着吴悠。吴悠手术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而我的心情也越感沉重,每天都是拉住吴悠的手不放,我真的害怕万一我放开,就再也抓不着了。没有任何事情能叫我感觉时间的残酷和无情,吴悠的父亲象几天就苍老了许多年一样。我根本不信神和命运,但每夜我却为吴悠虔诚地祈祷。吴悠也明显地感到了什么,每每和她询问的目光对视的时候,我都有种把她搂入怀里大哭一场的冲动。那天去看吴悠,是她手术的前两天。吴悠一天都没怎么说话,那种气氛更加叫我受不了。晚饭后,我陪着吴悠在花园里走,还是那条长凳,吴悠也依然坐在我的怀里。今天的吴悠没象往日般说说笑笑,只是很安静地坐在我的腿上,不住地用手轻抚着我的脸。草丛中蟋蟀在叫着,远处的黑暗中有几只萤火虫在飞来飞去。正当我在想说点什么来打破这种沉闷时,吴悠说话了:“要是我好不了,以后你还会记得我么?”我一愣,她的话有如一把大锤给我沉重的一击。难道她已经知道了么?在我询问与焦急的目光里,吴悠微微笑了笑,平静地说:“我自己最清楚了。我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那天我去打水,在楼道里听见两个护士在说我的病情。”一时间,我找不到任何安慰她的话语,只有更紧地抱住她,把脸埋在她的胸前。突然,一滴滴灼热的液体滴在我的脸上,我倏地抬起头,吴悠的眼泪象小溪般涌出她的眼眶。我慌忙笨手笨脚地为她擦去眼泪,心里不住地在说:不,不会的,她不会的。吴悠伏在我的肩头小声地哭着说:“怎么会是我呢?太不公平了,我还那么年轻啊。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一边轻轻拍着她,一边呼唤着她的名字并把我能想到的最肉麻的情话小声说给她听。吴悠这才抬起头,带着满眼朦胧的泪光看着我。“你知道么,”她说,“我就是因为你的这张嘴巴才被你骗到手的。我有时候都奇怪怎么会爱上你的。你一点都不可爱。还老欺负我。”我用手拭去她脸庞残留的泪痕,心里更觉的沉重了。接着,她说:“本来想你这次回来可以好好陪陪我,谁知道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早知道就不放你去国外了,就剩这么几天了,那怎么够呢?”说着,一串泪珠又涌了出来,她的声音哽咽着,“我不想做手术了,我好害怕。”“别哭,不会有问题的。”我轻抚着她的长发,鼻子在阵阵发酸。“可我还没准备好,我不想去死,我不想。”“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追问了半天,吴悠才告诉我,她听说隔壁病房的一个病人昨天晚上死在了手术台上。她还见过那个病人并且和她说过话。“不会的,你的手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相信我。”接着,我又说:“别说傻话了,我还打算寒假的时候带你去划雪呢。”“那万一”“别去想万一了,咱们去想那九千九百九十九吧。我早换了两副雪橇等着你呢。真的,就在我那边房间的柜子里。”“你用什么换的啊。”“长筒袜。”“是么?多少双才换一副啊?”“三十双换一副,两副就用了五十五双,还便宜了呢。”“我记得我没给你买啊?肯定是你本来想送别的女孩子的。”“是支军告诉我,我偷偷买的。”“那你送没送别人?”“送了,送给房东的老太太了。”“你肯定还送了别人,我早晚会查出来的。”“我说吴悠,别老这么不讲理啊。”“人家是病人么。”“那病人就可以不讲理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反正就这一次了么,再说了,我比你小啊。”我没再说话,把她慢慢搂在身边。她的长发依旧那么黑,那么柔软。过了半晌,吴悠轻声的说:“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我说:“其实,我也害怕。”“我会好的,是么?”吴悠趴在我怀里轻轻的问。“一定会的。”我的回答从来没有这么坚决过。我和吴悠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吴悠把头伏在我的肩膀上,过了许久,吴悠轻声的说:“不管怎么样,我认识了你,怎么也不亏了。”我没有再说什么,她的话给了我生命中最大的震撼,反而叫我平静了许多。我把她搂的更紧了。那一夜,我陪吴悠待到很晚,后来她开心地捧着我抓来的萤火虫。那一夜,月光如水。一天的时间过的很快,那一夜我失眠了。脑海里总是浮现着一具用白布遮盖的身躯,虽然是夏天,我在床上却瑟瑟发抖。对死亡的恐惧来自我身体的每一个毛孔,妈妈来看了我几次,安慰我要好好休息,因为明天还要给吴悠打打气才行。我尝试着入睡,但总被闹钟清晰的声音把我从迷迷糊糊里拉回现实。早上来到医院,吴悠的父母来的还要早,正先我一步在安慰着吴悠。吴悠的眼睛看着病床边的我,我也站在一边用心地注视着她。吴悠冲我招了招手,我来到她的床前。她张开小手,把我送给她的胸花放在了我的手中,“等我好了,你再给我戴上。”我点了点头,用力地把它攥在手心里。我拉着她的手,站在她的身边。她学校的好朋友和老师也来了,我感到她抓住我的手在出汗。“别怕,我就站在这里等你。”接着,我伏身在她的耳边说:“知道么,我爱你。”吴悠笑了,但她的眼睛里有种晶莹的东西在闪动。我和她的家人和朋友目送她被缓慢地推进了手术室。在护士副她上手术车的时候,吴悠用力捏了捏我的手,眼光格外的平静。我的眼光紧紧跟随着那辆车子,直到它消失在那扇门的尽头。那也许是我生命里最漫长的几个小时。楼道里的人很多却很安静。那个我在吴悠家里见过的男孩子也来了,我们友好地握手。他递给我一只烟,我点上并且很用力的吸着。我们都没有说话。我独自走在楼后面的那个小花园,前些天的每个黄昏,我和吴悠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坐在我们曾坐过的长凳上,心中感慨万千。阳光透过树丛洒在地上斑斑点点,我凝视着晃动的亮斑,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的清晰可见,整个天地仿佛清晰了很多,甚至于平时被我忽略的几盆花草在浓郁的阳光下也分外灿烂。在我身边仿佛有无数的生命在悄然孕育,又有无数的生命在默然消亡,我头一次感到自己站在生与死的的临界状态,一种莫名的感动从我心底涌出,洪水般在我身体的每个角落涌动。我忽然想起了那次在吴悠家里的争论。人,我必须承认,是积极的,就象是希望,在熄灭,也在燃烧,滔滔不绝,生生不息。我抬头望向手术室的那几扇窗子,刹那间,我清晰地感觉到她年轻的有力的生命的脉动,那感觉是那么的强烈和清晰以至于我感到自己的血液在沸腾澎湃,有如一线光明在大地边缘逐渐升起进而穿透云层万马奔腾般绵绵不绝永世不息。即便如此,在护士跑出来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的时候,有一种东西模糊了我的视线,我还是哭了。吴悠住了几个星期的特护病房后终于可以和我见面了。又过了一个月,吴悠被接回了家。而我开学的日子也快到了。我推着轮椅上的吴悠慢慢走在熟悉的街道上。那朵胸花也天天戴在她的胸前。上午的阳光温暖灿烂,无处不在。我听着吴悠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两年发生在她身边的故事。突然,“你看。”吴悠指着道路的另一边。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就在不远处的路边,在灿烂的阳光里,伫立着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你说呢?”我把手轻轻放在了她的肩膀上。“我在想,当初说不定我会去问你地安门怎么走呢。”说罢,她的小手也反过来搭在我的手上,回眸一笑,依旧迷人。完后记写完了这个故事,想起在哪个片子里听过这么一段话:“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东西永不消逝。”我躺在荒蛮的土地上看着你青春的流失,你站在光秃秃的小山上听着我的呼噜声传向四方来源水木清华站发信人,信区标题保重自己发信站水木清华站当我再次抓住吴悠的手的时候,我怎么也不肯放开了。我仿佛有很多的话要说,但除了静静地看着吴悠,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感觉她的手轻抚着我的脸,她的目光也紧紧的盯着我,嘴角露出了满足的微笑。“吴悠,这就是你和我们说的你的男朋友吧?也不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才那个冲我笑的阿姨说话了。吴悠回过头,红着脸笑了。“你看他怎么配的上你么,还是嫁到我们家吧,我表弟可精神了。”吴悠的脸更红了,还是笑。接着同病房的人都拿我开心。我也没办法反驳,只有跟着吴悠一起傻笑。午饭后,吴悠睡了一会,我看着她熟睡的样子,我轻抚她散在枕边的长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种想哭的感觉。好在吴悠醒了,她用毛巾被把自己裹起来,唯独把脑袋露在外面,大大的眼睛一眨一眨的看着我,这叫我想起了我在路上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醒了?”“醒了好久了。”“喝水么?还是吃点菠萝。”“我想去游泳了。”“等你好了我和你一起去。”“泳游不了,那我想出去走走。”“外面太热了,待会再出去么。”“我不,我想现在出去,老躺着背都疼了。”“那我去问问护士。”“德行。早知道就指望不上你。”我只有陪着笑握住了她的一只小手,坐在床边给她讲在莫斯科的很多故事。吴悠睁大了眼睛听我讲,我把很多故事讲的有声有色,病房里不时传出吴悠的笑声。晚饭过后,我才领着穿着宽大病服的吴悠来到楼后面的一个小花园里。“我要坐你腿上。”吴悠指着一个长凳撅着嘴说。我把吴悠揽坐在我的腿上,一手揽住她的小蛮腰,一手抓住她的一只小手。吴悠也双手搂住我,再没有当初在她们学校里那种战战兢兢和扭扭捏捏了。“你想我么?”吴悠问我。我没说话,把她搂得更紧了。“你知道么?我有预感你要来,真的。我总觉得你肯定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抱着很多的玫瑰。快说,玫瑰呢?哦,对了,你怎么好几个星期才给我来电话啊?真那么忙么?还是有了别的女朋友了?”我看着吴悠笑了,没说话。“我问你呢,你老笑什么啊?是不是做贼心虚?”我依旧没说话。“哎,你怎么才出去两年就真的变成鱼了?真的不爱说话了?”“那你还希望我象原来一样么?那你连插嘴的机会都没了,我是怕你回头自卑,所以才没说。”“才说你变好了呢,就知道你本性难移。不过,你瘦了很多。”说着她用手轻轻抚摩着我的脸颊。“还说我?怎么把自己给送医院里了?”“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晕倒了么。听她们说没什么大问题的。”“听谁们说的?”“是我的病友啊,她们都说住几天就没事了。”“听你父亲说还要做个很小的手术呢。”“看见你,高兴死了。”吴悠又象个小丫头似的,做在我的怀里不是揪我鼻子就是拧我的耳朵。接着她又说:“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么?”“是我们认识的时候吧?”“你怎么知道的?”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我都有点后悔了,那么快就成了你的女朋友了,一点过程都没有。我在学校的时候看别的男孩子追我们系的女生可辛苦了,天天在楼底下等。”“那我也去追你们系的女孩子,也辛苦一回给你看?”我嘿嘿的坏笑着。“你敢!”“追你的人也不少吧?我不问也知道。”“那当然了,可多了。”“你看你看,还沾沾自喜虚荣。”“你不虚荣啊?看你那会在我们学校拉着我昂首阔步的样子,我为好多人抱不平呢。”“是啊,是啊,是谁认识我就三天两头给我来电话?”“你?!那又是谁想把人扔在车站一个人回家?”我就知道翻来翻去她总得把这事情给抖搂出来,反正也没什么道理可讲,就用最笨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封住了她小小的嘴巴。一时间,我忘记了我们是在医院里,如果不是那股消毒水的味道,我们真的象回到了从前。在晚查房前,我把吴悠送回了她的病房,叮嘱她好好休息并且说我明天还来看她。“哦,差点忘了。”我从口袋里拿出在莫斯科给她买的胸花,放在她的手里。“听话啊,好好睡。”吴悠的笑容依旧那么迷人。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天天都去陪着吴悠。吴悠手术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而我的心情也越感沉重,每天都是拉住吴悠的手不放,我真的害怕万一我放开,就再也抓不着了。没有任何事情能叫我感觉时间的残酷和无情,吴悠的父亲象几天就苍老了许多年一样。我根本不信神和命运,但每夜我却为吴悠虔诚地祈祷。吴悠也明显地感到了什么,每每和她询问的目光对视的时候,我都有种把她搂入怀里大哭一场的冲动。那天去看吴悠,是她手术的前两天。吴悠一天都没怎么说话,那种气氛更加叫我受不了。晚饭后,我陪着吴悠在花园里走,还是那条长凳,吴悠也依然坐在我的怀里。今天的吴悠没象往日般说说笑笑,只是很安静地坐在我的腿上,不住地用手轻抚着我的脸。草丛中蟋蟀在叫着,远处的黑暗中有几只萤火虫在飞来飞去。正当我在想说点什么来打破这种沉闷时,吴悠说话了:“要是我好不了,以后你还会记得我么?”我一愣,她的话有如一把大锤给我沉重的一击。难道她已经知道了么?在我询问与焦急的目光里,吴悠微微笑了笑,平静地说:“我自己最清楚了。我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那天我去打水,在楼道里听见两个护士在说我的病情。”一时间,我找不到任何安慰她的话语,只有更紧地抱住她,把脸埋在她的胸前。突然,一滴滴灼热的液体滴在我的脸上,我倏地抬起头,吴悠的眼泪象小溪般涌出她的眼眶。我慌忙笨手笨脚地为她擦去眼泪,心里不住地在说:不,不会的,她不会的。吴悠伏在我的肩头小声地哭着说:“怎么会是我呢?太不公平了,我还那么年轻啊。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一边轻轻拍着她,一边呼唤着她的名字并把我能想到的最肉麻的情话小声说给她听。吴悠这才抬起头,带着满眼朦胧的泪光看着我。“你知道么,”她说,“我就是因为你的这张嘴巴才被你骗到手的。我有时候都奇怪怎么会爱上你的。你一点都不可爱。还老欺负我。”我用手拭去她脸庞残留的泪痕,心里更觉的沉重了。接着,她说:“本来想你这次回来可以好好陪陪我,谁知道事情会是这个样子。早知道就不放你去国外了,就剩这么几天了,那怎么够呢?”说着,一串泪珠又涌了出来,她的声音哽咽着,“我不想做手术了,我好害怕。”“别哭,不会有问题的。”我轻抚着她的长发,鼻子在阵阵发酸。“可我还没准备好,我不想去死,我不想。”“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追问了半天,吴悠才告诉我,她听说隔壁病房的一个病人昨天晚上死在了手术台上。她还见过那个病人并且和她说过话。“不会的,你的手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相信我。”接着,我又说:“别说傻话了,我还打算寒假的时候带你去划雪呢。”“那万一”“别去想万一了,咱们去想那九千九百九十九吧。我早换了两副雪橇等着你呢。真的,就在我那边房间的柜子里。”“你用什么换的啊。”“长筒袜。”“是么?多少双才换一副啊?”“三十双换一副,两副就用了五十五双,还便宜了呢。”“我记得我没给你买啊?肯定是你本来想送别的女孩子的。”“是支军告诉我,我偷偷买的。”“那你送没送别人?”“送了,送给房东的老太太了。”“你肯定还送了别人,我早晚会查出来的。”“我说吴悠,别老这么不讲理啊。”“人家是病人么。”“那病人就可以不讲理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反正就这一次了么,再说了,我比你小啊。”我没再说话,把她慢慢搂在身边。她的长发依旧那么黑,那么柔软。过了半晌,吴悠轻声的说:“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我说:“其实,我也害怕。”“我会好的,是么?”吴悠趴在我怀里轻轻的问。“一定会的。”我的回答从来没有这么坚决过。我和吴悠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吴悠把头伏在我的肩膀上,过了许久,吴悠轻声的说:“不管怎么样,我认识了你,怎么也不亏了。”我没有再说什么,她的话给了我生命中最大的震撼,反而叫我平静了许多。我把她搂的更紧了。那一夜,我陪吴悠待到很晚,后来她开心地捧着我抓来的萤火虫。那一夜,月光如水。一天的时间过的很快,那一夜我失眠了。脑海里总是浮现着一具用白布遮盖的身躯,虽然是夏天,我在床上却瑟瑟发抖。对死亡的恐惧来自我身体的每一个毛孔,妈妈来看了我几次,安慰我要好好休息,因为明天还要给吴悠打打气才行。我尝试着入睡,但总被闹钟清晰的声音把我从迷迷糊糊里拉回现实。早上来到医院,吴悠的父母来的还要早,正先我一步在安慰着吴悠。吴悠的眼睛看着病床边的我,我也站在一边用心地注视着她。吴悠冲我招了招手,我来到她的床前。她张开小手,把我送给她的胸花放在了我的手中,“等我好了,你再给我戴上。”我点了点头,用力地把它攥在手心里。我拉着她的手,站在她的身边。她学校的好朋友和老师也来了,我感到她抓住我的手在出汗。“别怕,我就站在这里等你。”接着,我伏身在她的耳边说:“知道么,我爱你。”吴悠笑了,但她的眼睛里有种晶莹的东西在闪动。我和她的家人和朋友目送她被缓慢地推进了手术室。在护士副她上手术车的时候,吴悠用力捏了捏我的手,眼光格外的平静。我的眼光紧紧跟随着那辆车子,直到它消失在那扇门的尽头。那也许是我生命里最漫长的几个小时。楼道里的人很多却很安静。那个我在吴悠家里见过的男孩子也来了,我们友好地握手。他递给我一只烟,我点上并且很用力的吸着。我们都没有说话。我独自走在楼后面的那个小花园,前些天的每个黄昏,我和吴悠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坐在我们曾坐过的长凳上,心中感慨万千。阳光透过树丛洒在地上斑斑点点,我凝视着晃动的亮斑,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是那么的清晰可见,整个天地仿佛清晰了很多,甚至于平时被我忽略的几盆花草在浓郁的阳光下也分外灿烂。在我身边仿佛有无数的生命在悄然孕育,又有无数的生命在默然消亡,我头一次感到自己站在生与死的的临界状态,一种莫名的感动从我心底涌出,洪水般在我身体的每个角落涌动。我忽然想起了那次在吴悠家里的争论。人,我必须承认,是积极的,就象是希望,在熄灭,也在燃烧,滔滔不绝,生生不息。我抬头望向手术室的那几扇窗子,刹那间,我清晰地感觉到她年轻的有力的生命的脉动,那感觉是那么的强烈和清晰以至于我感到自己的血液在沸腾澎湃,有如一线光明在大地边缘逐渐升起进而穿透云层万马奔腾般绵绵不绝永世不息。即便如此,在护士跑出来告诉我们手术很成功的时候,有一种东西模糊了我的视线,我还是哭了。吴悠住了几个星期的特护病房后终于可以和我见面了。又过了一个月,吴悠被接回了家。而我开学的日子也快到了。我推着轮椅上的吴悠慢慢走在熟悉的街道上。那朵胸花也天天戴在她的胸前。上午的阳光温暖灿烂,无处不在。我听着吴悠滔滔不绝地讲着这两年发生在她身边的故事。突然,“你看。”吴悠指着道路的另一边。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就在不远处的路边,在灿烂的阳光里,伫立着一个美丽的女孩子。“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你说呢?”我把手轻轻放在了她的肩膀上。“我在想,当初说不定我会去问你地安门怎么走呢。”说罢,她的小手也反过来搭在我的手上,回眸一笑,依旧迷人。完后记写完了这个故事,想起在哪个片子里听过这么一段话:,,“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东西永不消逝。”我躺在荒蛮的土地上看着你青春的流失,你站在光秃秃的小山上听着我的呼噜声传向四方
生是色狼,死是色鬼。
|

5D公害
职务:普通成员
等级:9
金币:10.3
发贴:36272
注册:2002/1/13 9:52:57
|
#22002/9/30 15:41:38
秋冰梦,这不伦不类的物事
|

秋冰梦
职务:普通成员
等级:6
金币:5.0
发贴:4325
注册:2002/5/16 22:14:21
|
#32002/9/30 15:50:18
兔子的嘴~真大!
生是色狼,死是色鬼。
|

IT编辑
职务:普通成员
等级:6
金币:10.0
发贴:7769
注册:2002/4/1 10:30:23
|
#42002/9/30 16:06:28
不大,不大,我们不嘴不大,顶多也篮球那么大
|

27岁高龄的东方脑力衰
职务:版主
等级:6
金币:24.0
发贴:4053
注册:2002/6/30 17:00:0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