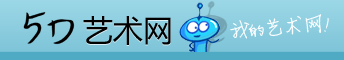#12003/4/12 13:08:43
(两年以后)
当我觉得需要去了解人家想点什么的时候,我决定去窃听。
当我觉得需要点什么东西来充实一下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我决定去恋爱。
因为快毕业了,我要留点回忆做纪念。
首先,我需要确定一个目标,是我自己去寻找,还是等目标自己出现?
……思考中。
哟,头好晕,大概是今天晚上喝多了。我怎么躺床上了?
终于考完了,以后再没有考试来烦我了。
其实,今天早上我早就做完了试卷,不会做的我懒得去想;就等着考试时间到交卷纸。
大概其他同学也在等,监考老师也在等。
监考老师大概在怪我们怎么还不交卷,因为现在考场里没有一个人在答题。我的目光无聊的四处乱扫,我还发现很多和我一样无聊的眼睛,也在看来看去,偶尔目光相遇,大家脸上才出现一点兴奋的神色。
老师也真是。我们的试卷还没有写完,怎么能交呢?剩下的都是不会做的,当然就不做了。这题目想也想不出来,除非拿书来看,所以我们只能四下乱看了。
可是老师偏偏以为我们都在和他作对。
好在,考完了这一门,就没了。接下来就是毕业设计。
终于完了,其实我很不愿意结束的铃声响起。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毕业生该做什么?我们空有疯狂的欲望,却找不到疯狂的感觉。 他们找不到感觉,有的是因为没有恋爱,有的是因为正在恋爱。 我找不到感觉之一是因为我很惨,毕业设计分到一个很没劲的,没人要的。
直到今天喝醉了,我才找到一点毕业的感觉。
我觉得,从酒馆到学校宿舍的路可真远。
我大概真的是喝多了。
下午我们进了学校旁边那个“犀园酒楼”的时候,都快六点了。小姐把我们领到了他们最大的包间。十来个人。
先来了水煮花生米和土豆丝各三个,这是老规矩;然后是热菜若干;白酒——我记不得了,好象是孔府。
几杯下肚之后,有人上脸了,有人兴奋了,开始分成几堆,讨论三年半的恩怨情仇,当然,醉话而已。魏春红着脸拉着我,说我这人还够朋友,但对人总是滑头,我说他重色轻友,最后两个人各干了两杯,言归与好;然后他开始说他那年追求夏小郁的事。那边老六和赵文伟也在拉拉扯扯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老八也和其他人频频举杯。
大家又起立干了一杯,大概是祝以后怎样怎样。然后有人拿过卡拉OK话筒开始,唱歌,唱着有人开始抢话筒,怪腔调里充满酒气。
刘勇点了一个《国际歌》,唐朝的。大家开始高声齐唱国际歌,十几个人的声音震得天花板直掉灰。“英特纳雄耐尔就一点要实现……”,还没等唱完,小姐敲门进来了,要我们小声一点,所有的客人都提意见了。
有人继续唱歌,有人边吃边说。到后来有人开始哭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候才有人发现,怎么没有拉女生一起来?大失误啊。
我一直不知道那天谁结的帐,我只知道我把自己的五十元交了出去。后来我也没问过,不想让人家再来找我要钱。
回来的时候有几个已经走不动了,我架着刘勇,吴志明架着赵文伟。我扶着刘勇过马路的时候,深感力不从心,他毕竟比我重二十来斤,我的腿也有点软了,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有些害怕。老六在后面唠叨:“谁也别拦着我……”。
头很晕,但我睡不着。他们几个也还没睡,几个人在说什么疯话。
老四在说他的罗曼司,红红的醉眼象两个单摆晃来晃去。
他说他一共花了两百多来请她吃饭。
他说他一共给她写了十来封情书。
……
正等着他的下文,电话响了,醉鬼接了电话,然后朝对我说:“找你的!嘿嘿,女生。”
等我接完电话,醉鬼们就让我老实交代,我又勾引了谁。
“呸!什么叫勾引啊,还‘又’。是吕薇,问赵文伟呢,问他是不是喝多了。”我挂了电话,回倒自己温暖的上铺。
“她干吗问你啊?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不问老赵?”醉鬼不依不饶。
“因为我忠厚老实。瞧你那样,听见女的说话,魂都没了。”
对啊,为什么要问我呢。对他们我可不能说。原因说来话长了。
两年前,我们曾经往她们宿舍放过窃听器;当时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那次放假回来之后,本来我们是打算继续窃听的,但我再没有去放,因为吕薇有一天下午找到我。
“哎,你老实说,我们屋的无线话筒是不是你放的?”教室里没人,她开门见山。
“……,是。”我吃了一惊,但还是痛快的承认了,当时我想到了学工部,还有各种处分,甚至开除。
“为什么要放?”
“偷听呗。”
“为什么要偷听?”
“为了了解女生思想动态,好做思想工作。”
她扑哧笑了一声,又严肃的问:“什么时候放的?”
我如实交代了,然后,我问她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我们都是╳呐?我自己收听到的!”她说。
其实我们早就应该想到这个结果,因为我们在收听的时候,可能全校的人都能收听到;可能有人会以为又有一个新的电台开始广播了,而且内容全都是聊天节目。这样的窃听真是愚蠢。
“你们什么时候发现的?她们都知道吗?”我觉得事情可能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糟。
“我知道,是上个学期放假前一个月吧;她们知到不我也不清楚,反正我没告诉过她们,她们也没有跟我说过;跟你说过?”
“没有,你打算怎么办?不会告我们吧。”我假装镇静,其实早乱了方寸。
“我不告你,放心吧;不过我求你一件事。”她的表情不严肃了,笑吟吟的看着我。
十分钟后我就成了吕薇的窃听器,负责帮她收集男生宿舍所有和她有关的言论,还要关注她的男友赵文伟的一举一动;这个任务也让我和老赵成了相当好的朋友,当然也方便了对他的监视。从此,他和她柔情蜜意的时候,我的任务就轻一点,要是遇到俩人猜忌甚至闹别扭,我的任务就十分繁重。耻辱啊!
后来我定神想了想,好象我们窃听的时候从来就没从破话筒里听到过吕薇的声音。其实我们无聊的时候也想过,哪天再把那窃听器再放回去,满足一下自己的偷听欲,但我却不敢放了;我骗他们,等快毕业了再说,那时候没人管,也有时间偷听;也不知道他们忘记没。
似乎酒醉之后都醒得格外的早,这一次也不例外,我醒来的时候,才六点不到。老八也醒了。突然发现老六的床是空的,摸摸,凉的——他昨天可能一夜没回来,我完全把他忘记了;老八也说没看见他。我回忆了一下,昨天老六是跟在我和刘勇,吴志明和赵文伟的后面,但回来以后就没有看到他。我把大家都叫醒,谁都说不知道;于是急忙分头去找。
我一进613,一看,吃了一惊,吴志明被绑在床上,还没有醒。他手脚都被绑到上铺的床沿上,成一个大字。一问才知道,昨天晚上他又跳又闹,在床上翻滚不停,外加呕吐,下面的只好顶着脸盆接着;被他吐了一身,连下铺的被褥也不能幸免。后来没办法只好把他绑起来。
我到各屋去问,都说没看见老六。死哪去了?
我们又发动了不少人去找老六,还是没找到。到7点多的时候,我终于接到了电话,说老六被找到了,他在女生楼过了一夜!
怎么回事?被女生抓住了?先去把他接回来再说吧。
从女生宿舍到男生宿舍,有20多米;从男生宿舍到女生宿舍,也是20多米。
为什么老六会晕了头走到女生楼呢?
他醉了,但醉了不能作为辩解的理由,如果学校知道,他就惨了。
我们把老六接了回来,问了他,并且问了女生,才明白昨天晚上出了什么事。
事情其实和大家想象的差不多。
昨天晚上我们一起从酒馆回来的时候,老六晕头晕脑,不小心掉到了路边挖了准备栽电线杆子的坑里,我们都不知道。这家伙掉下去以后,没有爬起来,在坑里睡着了。估计十二点多的时候给冻醒了,然后晕头转向,走到了北二楼;北二楼就是女生楼,我们住北三楼;然后他硬撑着上到六楼,找到613,“邦、邦、邦”,敲门。
听613的女生们说,当时她们都睡着了,突然听见有人敲门的声音,然后醒了三四个;听听有个男说话的声音,她们吓坏了,没敢开门。不久就听见有人打鼾的声音——老六在门口睡着了。于是她们插紧门继续睡觉。
我一直搞不清楚,老六是怎么上到女生楼的。按理说,女生楼的门是要11点以后是要关的——至少值班的老太太也要看着吧,他怎么上去的?
老六说他记不得了,说他就是走了上去,没有任何人管他,他敲门,没人开,他就坐在门口等着,醒来已是天亮了,旁边站的是罗惠和许丽娟——她们把他推醒的,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一身黄泥坐在女生宿舍的六楼。
之后的几天,老六视死如归,就等着斩首示众。但女生们一直没有把这事捅到学校,这大概是咱们班女生竭力活动的结果,当然也有楼管老太的功劳,她可不想让自己的工作疏忽被领导知道。
毕业设计正式开始了,但我没有教研室,只能到图书馆;没有分给自己的计算机,只好上公共机房;好在不花钱,否则我就不干了。同病相怜的还有七、八个同学,以后的日子就是大家一起在公共机房混了。
我常用的是机房西南角上的台机器。没什么特别的。
唯一特别的是她的机器离我很近。
其实我开始也不是因为道这个,只是自己在上面装了专用的软件,懒得再到其他地方装,而且这里做什么管理的基本上都看不见。时间一长,大家使的机器就差不多也固定下来了。
每一天都可以看见她。每一天,我看见她的时候,总是会想起两年前摇晃的火车上,幽静的晚上。
那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她已醒了,坐在旁边看书。后来我一直想,她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别人怀里,会怎么想呢?
我很担心她会认为我是个好色之徒,找机会占她便宜。
或许她醒来的时候,已经没有靠着我了;这样也不错,但总觉得不太满意。
我决心毕业前要问她一问,这需要勇气;虽然我和她挺熟,但还没熟到那份上。
什么时候问呢?怎么问?
老赵在和我一样在公共机房搞设计,吕薇也是,我的监视任务就轻了许多;唉,毕业以后一定要找个机会向老赵道歉。
这天晚上,我挺无聊,和老八上到楼顶去转悠。房顶上已经有两三个人了,他们拿着望远镜在朝礼堂那边看,我也跑过去,埋伏起来。
“看什么呢?”
“呵呵,好看的呗,有俩人……”
“在那里啊?”
“礼堂大门,嘘……小声,不要让他们听见了。”
“什么啊?快给我看看。”我顺手抢过一只望远镜。
我看见他坐在礼堂的台阶上,吕薇和老赵坐在那里,不知道在说什么,过了一会吕薇站起身来,很生气的样子,把包向他扔过去;老赵也站起来,俩人不知道吵些什么;然后……我手里的望远镜又被别人抢走了。他俩也离开了礼堂大门。大家在楼顶上向老赵吹口哨。
“她看见咱没有,一抬头不就看见啦?”
“你管那么多呢!”
“唉,我老觉得早上起来没多会又要睡了……堕落,真没意思。”老四关了灯,感叹说。现在毕业生宿舍晚上都不停电了,但要求关灯(是不是有点无理?)。老七、老三、老二也搬走了,这学期多出来几间空屋子。
“刚才我看见老赵和吕薇不知道在礼堂那边吵什么,你说,现在这吵架的怎么就多起来了?”
“可想而知啊……”
我又想起老四醉酒时说的二百多元的饭局和十来封情书。
“老四,继续说你啊,你那天的饭局和情书。”
“什么饭局情书?”老四不知真忘了还是装傻。
“少来这一套,快说快说,大家都等着呢。”老八的眼镜在黑暗中闪闪发光,他还在看学校bbs上的帖子。
“没有啊——什么啊?”
“当然是追女生的,说不说,我靠,刑法伺候,让你见识见识满清十大酷刑。”老六和老大坐起来,床吱吱嘎嘎的响。
“谁敢,谁,别闹啊!老六,当心我告你夜闯女生楼,图谋不轨!”
“恩?敢抗日,上啊!”
经过十秒的酷刑,老四开始招供了。
“我没带她上‘犀园’,去的是在西门边的那个‘怡风’,怕给咱班人看见;还去了‘心动’……”
‘怡风’是个酒楼的名字,平时我们几乎不去那;心动酒吧,我们更是从来不去,没那心情。
“去过几次啊?”
“能有几次啊,不就一次吗;先去吃饭,完了上酒吧。”老四的声音听着好象很委屈。
“就一次啊,你可真让人失望。”老六似乎幸灾乐祸。
“没上山上,树林里走走?”老大关心的问。
“上树林?我可不敢,情不自禁我做出什么坏事怎么办?可能她也不敢。”
“那情书呢?接着说。”老六接着问。
“喂!老四,你说半天我还不知道你说的她是谁呢,先说说那美女是谁?”老八转过头来问。
“对,先说,是谁?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要素给忘了。”老四也问。
“这个我知道,是咱们校花对不对?”我慢悠悠的插话。
“你怎么知道?不会是她跟你说的吧?”老四奇怪的问。
“校花都不认识我,跟我说什么啊?我自己猜的。你们还记得那天咱们窃听到的那个,有人要请校花吃饭的事吗?”我有这么聪明?我是听吕薇说的罢了。
“我靠,老四你就是那个把人家吓得扭了脚的人啊,哈,我怎么就没想到是你呢。”老六说完,笑得花枝乱颤。
“咱们还讨论过追求会不会成功,是吧?”老大说。
“什么时候啊?有这回事吗?对了,你再说说那情书。”老八想不起来了。
“你慢慢想吧。各位,求求大家了,给我留点面子吧。”老四觉得面子挂不住了。
“别啊,老四;大家不是取笑你,是想法帮你呢。上次你怎么一次就放弃了?”
“不提了,当年年少无知……”老四一肚子沧桑。
“别啊,老四,现在你也有机会啊,她不是也没男朋友吗?”
“别诱惑我了,我现在心里难受……”
“对,要毕业了,试试,别给自己留什么遗憾。”老大也劝他。
“啊!……我受不了了!!!”
“小声点!”
“好吧。试试,不过没信心。”老四一副蔫巴样。
“我还记得你那次回家,三女一男,你说说吧,你在车上都干了什么?”老四停了一会,忽然问我这事。他开始反击了;老六他们也等着听我的回答。
“那次啊……”我假装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干什么?我到是想干,能干的都干了,不能干的都没干。你倒是想想你怎么干吧。”
“怎么干?你说。”老四其实心里挺想,就是有点心理障碍。
“我觉得啊,在学校这种地方,绝对不能拉近咱老四和校花的距离;最好是出去玩。”
“出去玩?还得花钱;谁说在学校里不能恋爱,你瞧星期五下午女生楼下面,那男生聚得跟看发榜的差不多。”
“那些都是俗人!咱老四什么人,校花什么人,三年半没谈恋爱为什么呀?就是瞧不起那些俗人;老六这办法我觉得好,但是——怎么实行,得研究研究。”
“老四,咱们都可以帮你……”老六来这个可是老手。
“帮我?那先借我点钱吧。”
“去——我说得是,你们要出去玩,我们可以陪你去……”
“嘿,老六,人家老四的事,你去干吗?是不是居心不良?”老大倒是很警觉。
“靠!你说什么啊?你想想,你第一次约人家出来,校花绝对不会去;特别啊,是咱们不能去近的,什么西山,颐和园啦,要去就去远的,比如青岛、北戴河什么的,去得越远,关系就能拉得越近;咱们宿舍一起去,叫上她和它们宿舍那几个女生;怎么样?到时候给你们创造独处的条件,嘿嘿。”
“去哪里?青岛好啊,我一直没去过呢。”老八很兴奋。
“老六真高人也,不过去泰山也可以啊,晚上爬泰山,嘿嘿,给你机会。”我也出了个点子。
老六对我说:“请人出去玩还要看你的,她们宿舍你有熟人啊;她不跟校花关系挺好,到时候你得去求她帮老四忙啊。”
“话我是肯定会说的,不过我可不敢保证她会答应。”我说。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其实你也是有机会的啊,你那心思我还看不出来吗?到时候,咱们也会帮你的。”老六真是人精,他的话说得我的心也痒痒。
“对了,为了帮老四追到校花,我提议,咱们恢复窃听怎么样?”我提议。
“好啊,那玩意我还留着呢。”老六跃跃欲试。
“不过,我觉得咱们这次任务重大,得换个好的了,原来那太破了,老听不清什么,关键时刻就掉链子。”我说。
“这好办了,老四,你的毕业设计不就和什么窃听有关系吗。”
“我说你们这么好心帮我呢——原来要我帮你们做这个啊。得,做就做吧,原材料还可以报销,哈。图是现成的,大家一块弄。”
“对了,不能再做一般的收音机能收到的了;太不保密了,咱们这次的可全是重要机密啊!”
“那还不好办,把发射频率调开点,收音机不就收不着了;接收的也做一个,或者弄个收音机来改改。”老四是准专业水平。
“谁要泄密,酷刑伺候!”
说了半天大家兴奋不已,躺在床上睡不着,又开始给老四支招,每人也分配了任务。最后大家决定,约她们宿舍的人出去玩,就去青岛,或泰山;日子就定在五一。或许这次我能有机会问我早想的那个问题。
明天就要开始做准备,五一前要把新的窃听器弄好。还要先想办法约上女生,别让她们被人先约了去。
对了,老六一向滑头,今天晚上怎么这么热心?
奇怪。
春暖花开。
每天我都起得挺早,到了机房,先开机,等着机器启动的时候,再到各座和同学嘻嘻哈哈,说大半天再回去,——那破机器启动实在太慢。一般我坐下开始做设计,她才拎个包进来,点点头,然后在我身旁坐下;时间长了,我常和她开点玩笑,还偷她包里的润喉糖吃,抢她带来的水喝,然后坐下看她生气的样子。
现在最大的好处是到食堂不用排队了。看看时间差不多,就关机走人,一堆人直奔食堂而去,等着食堂开伙;咱一个班的就在食堂占下几张桌子,好菜共享,说说笑笑,好不痛快;等我们吃差不多了,才见学生们拥进食堂。说起前几年人满为患,我们还在食堂排队的时候,老六自作聪明,弄了顶白帽子戴上,冒充回民到回民食堂打饭,久而久之被大师傅发现马脚,险些被扁,不觉好笑。
毕业生的日子过得也挺开心。
当然了,还要做窃听器。
其实,做个能窃听的东西是挺简单的;难的是做一个效果好,体积也不大的;自己做,也不能要求功能太多。每天做毕业设计,总要有半个小时以上是在老四的教研室里度过,一块忙着做窃听器;这次,老四承担了主要的工作,我们只是和他一块去西四买元件什么的,然后帮他检查电路,实验实验。比起我们来,他可是专业水平。
我也有我的艰巨任务。
我们五一要出去玩的消息我早就先透露给了吕薇,问她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吗,她回答说和我们去没意思——大概人家想和老赵一起去。
然后告诉她,这好办。
在机房我借偷润喉糖的机会对她说,我们宿舍五一要去青岛或者泰山。
“好啊,我也要去,我还没去过那地方呢。”她的反应让我感到格外惊喜。
“那你可要做好准备啊,主要是钱。不行我可以借给你。”
“不会就我一个女生吧?那我就不去了。”
“我去叫上吕薇,你就去?最好啊,能多叫上几个你们宿舍的女生。”我说完,走到吕薇机器前,拍拍她的显示器。
“吕薇,你看见了吧,你要不去她也不去,你俩要不去。一个女生我也请不来。你就看在我帮你当了两年特务的份上,我算求你了,帮我,不是,帮我们宿舍这忙吧。”小声的说生怕她和其他同学听见。
“怎么回事,没那么严重吧?”
“走出去说。”我和她出去,我很担心老赵看见;他看见了,没有什么反应;我们下楼找了个空教室。
“其实,你应该知道,这次,我们是为了我们老四和校花的事,你也知道。”
“你们想帮他啊?我也告诉你,这事希望不大。”
“只是想让老四大学毕业没什么遗憾;你说我们老四,他不是没收到过情书、纸条,为什么人家这些年没那个?不是就因为还想着她吗;这次她俩要成了当然好,成不了就当好梦一日游了——这忙你一定得帮。”
“我看你没那么好心吧,我早看出你什么心思了;还惦记着她呢,是吧?”
“是。”我回答得很干脆;我发现有些想法自己以为掩饰得很好,但别人早已知道,说与不说而已。
“好吧,我帮你们说说,试试吧,帮你叫上她,还有校花。”
“多几个也无所谓啊。”
一起回到机房的时候,老赵看到我,冲我树起中指,我也冲他甩出一个“V”。
“做准备吧,吕薇也去。”回到座位我对她说,“需要钱早说。”
“好啊,你们快去取钱吧。”
老四的活挺慢,过了好一段,窃听器还没做出来;让我们都挺不满,其实也不能怪他,他那老师逼完他的开题报告,又天天盯着他的设计进度。
这天早上我起得有些晚。等我们进了机房的时候,发现今天的气氛完全不对,里面乱糟糟的。猛然想起,现在是4月末了,今天几号来着?cih发作了?事实证明了我的感觉,机房有若干台机器中招了,男生拍着键盘骂骂咧咧,女生对着显示器惊慌失措。当然也有一部分机器没事,比如我的,虽那上面的cih一抓一大把,杀也杀不掉(其实我也懒得管),但那防火墙总算有点用;打开,破机器安然无恙,虽然启动仍然很慢。机房的管理员手忙脚乱,还不停对那些倒霉蛋发火——其实,他服务器上提供的大部分软件,都有病毒。
过了一会,我才明白我比起那些倒霉蛋并不幸福;她的机器也用不了,这些天都不会来我身边坐了。因此我决定,也不来这破机房了,去老四那帮他的忙,要不去老六老八的教研室上网去。嘿嘿,还可以专心的准备五一计划。
下午吕薇告诉我校花同意一起去了,要约个时间,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可事情并没有这么顺。
到了大家一起讨论的时候,她们反悔了,说去青岛太花费贵了;我们说,可以借你们钱;她们说,借了还是要还的;我们说,不还我们也没意见。
其实她们好象在找什么借口。我急了,问她们,多少才不贵?泰山行不行?
回答说,还是贵。
经过讨价还价,谈判最后的结果是,去野三坡。
对这个结果大家都很不满意,但去总比不去好。
“哎,没劲。”老八还是一心想去青岛。
“将就一点吧,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老大说。
“嘿嘿,吃豆腐?你真有口彩。”老六一脸坏笑的说。
明天就出发,不等五一,那时候火车会挤死人的;计划是中午的火车,丰台火车站上车。
接下来,就开始准备东西了;其实这都是女生的意见,她们有要买的若干东西,从果酱到吊床、桌布,几乎象去野营。大家先凑了钱,让我和她去买——因为我俩这几天都不能去机房搞设计,机房那些机器都回厂修理去了。
其实,说是我和她去买东西,只是让我去做个苦力;不过,陪女孩子逛街,感觉也不错。买完东西,快七点了,我俩还在街上吃了晚饭,然后坐电车回学校;车上,坐一块就跟在火车上差不多,我一直想问那天在火车上的事,但等我稍微有点勇气的时候,车到站了。
我回到宿舍,老四亮出了他做好的窃听器;不错,比原来那小多了,外壳用的是我原来那个数字呼机的外壳。
“你什么时候把我的呼机拆了?”
“今天下午。看你这大小刚好合适,反正你也有新的啦。看看,外型很有欺骗性吧?按键就开始工作。”
“天……,我前段投出去的简历写的都是这数字机的号呢!你害死我了。那接收机呢?我看看。”
“喏,也是用你的收音机改的,只有你的收音机最灵敏……”
好事总是多磨。这次似乎也这样,一起床,事情又发生了变化。早上班长进了屋说,今天下午本系要开会,不要缺席;据说是要传达什么重要消息。
怎么办,还按原计划,中午去野三坡吗?
我们一合计,管他的,照样去,这次机会不可失啊!再说了,系里开会那点事,管得了毕业生?
女生也来电话了问,我们的答复是,先做好走的准备。
“其实晚一天走也没什么啊,今天就开会吧。”老大说。
“你说的倒是不错,可昨天兴奋了一晚上,今天就被它这么一扫兴,心里实在是难受。”老八说。
“我也是,不爽啊。”我和老四都觉得系里很跟我们过不去。
“系里在礼堂开那会啊,没什么重要的;都开多少回了,去了还不是去打瞌睡;我说,照样,今天,吃了饭就走。”老六不以为然。
11点多在食堂遇到吕薇她们,我们坐一块吃饭。
“怎么办啊,下午要开会,咱们还去吗。”吕薇问。
“当然去啊。”我说。
“开会怎么办?”
“别怕,我们去找老师请假。哎,看,韩书记在那。”老六胸有成竹,拉上我朝系里的书记老太太坐的桌走过去。
“你真请假啊,怎么请啊,说请假出去玩啊?”我急了。
“急什么,听我说,你机灵点。”
到了书记饭桌前面,老六必恭必敬的叫老太太:“韩书记……”
“什么事啊?”老太太很和蔼,放下自己的勺。
“韩书记,是这样啊,我们在那个,在咱们系的公共机房做毕业设计;这几天机房的机器都染病毒用不了了,设计也做不了,您看看能不能跟五系的老师说说,让咱们用用他们五系的机房,他们系的机房很空的。”老六瞎说一气。
“哦,”书记老太想了想说,“这样吧,今天星期五了,星期一是五一,星期二我去说说;要是可以,我就告诉你们班主任,你们班主任是毕老师吗?”
“是,谢谢啊,韩书记。”
“现在不能用机房,你们也要好好做设计,多跑跑图书馆,……,吃饭去吧。”和蔼的老太太又说了半天。
我们一付凯旋的样子,回到饭桌前。
“她同意没有啊?你们说大半天。”她端着饭盆,问我。
“当然了,书记和他是老乡啊。”老六指指我。
“真的?”
“不信啊?你去问她好了。嘿嘿。”我觉得这大概不是撒谎吧。
“好了,假也请了,吃完回去拿了东西就出发。对了,刚才书记说了,出去的时候,别声张,注意别给别人知道,影响不好。12点半之前,北门见面啊。”
北门,我们五个在等女士到来,焦急又耐心。
“老六真有你的!”老四知道了老六的花招以后,很佩服。
“是,花招都耍到韩老太身上了。”老八也是,五体投地。
“让书记老太太知道,你就倒霉了……”老大真是胆小。
“嘘,别说了,来了来了……”
“可不能让她们知道。知道就完了。”
她们一共来了四个人,她,吕薇,校花,还有一个,是罗惠。
“罗惠,你也去啊?”老大笑嘻嘻的,问。
“不让我去啊,那我回去吧。”
“哪能呢——都到了,想想拉什么东西没?……没有?那走吧。”老六成了核心了。
我算明白老六怎么这么热心出去玩了,班上谁都知道他和罗惠的关系跟苍蝇拍和苍蝇似的。
刚上火车,上人挺少;怎么安排座位呢,四女五男。女生们先用纸巾把座位揩干净。
“哎哎哎……你们这是怎么坐啊?”老大发话了,“来来来,一男一女对着坐。”
“嘿嘿,真是羊入虎口啊,你们逃不了啦。”老六呵呵假笑。
“去,去……”
最后局面:左边,我,老四面对她和校花;右边,罗惠对老六,吕薇面对老大和老六。
对着坐远没有排着坐舒服是不是?老大真是╳。
浪漫之旅从此开始?说什么啊?这样坐法好象是在谈判。
“哎,听说去野三坡的人挺多,咱们要是找不到地住怎么办?”还是吕薇先说话了。
“那家庭旅馆多了去了,担心什么啊,要是真找不到地住,也只能在空地里过夜了。”
“好啊。空地就空地,看星星多浪漫。”校花的话让老四回味无穷。
“这么多年,咱们还从来没一块坐过火车呢……”老大感叹说。
“未必啊,他俩坐过长途呢……”老四老六看看我,又看看她。
“是啊,一个人和三个女生一块,幸福吧?”大家一起起哄。
“左边坐一个,右边坐一个,前面再坐一个,对了听说你们那同学挺漂亮?”老八问她。
“这你们都知道了?他说的?”
“是;他说,很漂亮,但是没你漂亮。”老六把她说得满脸幸福。
“在火车上你们干吗呢?”一个女生问。
“算命啊,只算爱情。”我说
“快快,给我算算。”吕薇说。
“没扑克啊?”
“我有——别算命了,打牌吧,拖拉机。”老大的牌瘾上来了。
大家开始打牌,不过刚铺开牌局,车就停了,下面跟逃难似的上来一堆人,背着大包小包,还有人带了一筐烧鸡、盒饭,就地卖开了。刚才的空座转眼就无影踪了,连中间的过道也挤得满满的。我们这边,我和校花换了座位,这样,我和老四都分别坐到两派座位的外面,让两个女士坐到里边;这样不但可以护花,还方便私下说话。不知道老六那边怎么样了,过道挤满了,一点看不见他们。
到了野三坡,下火车的时候,突然发现车门口没有站台,离地很高;男生都一跳而下,然后把女生一个个接下来。
天色近黄昏,由老大和老六去找住处,其他几个拿着包在河滩边等他们。他们去了很久,我们无聊的去看河里的小鱼,水很清,小鱼密密麻麻,相互之间开玩笑消磨时间。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回来了。
“怎么样啊,找着地住没有?这么久。”我问老六。
“旅馆都满了,农民家里也满了。”老六脸色严峻。
“都被出来玩的学生定下了。”老大补充。
“怎么办啊?真在空地上过夜了?惨了”她问。
“没那么严重,我和老大找了个农家,多给了点钱,有了大炕睡了——人家把自己睡的让出来了;不过啊,只能九个人挤一大炕。”
“不会吧……”女生齐声叹道。
“放心吧,我们都是正人君子。”